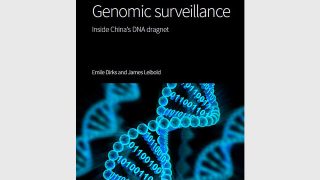詹妮弗·潘的新書展示了中共如何以「消除貧困」為藉口,利用其「低保」這一民生保障工程進一步監視政治和宗教異見人士。
作者:馬西莫·英特羅維吉(Massimo Introvig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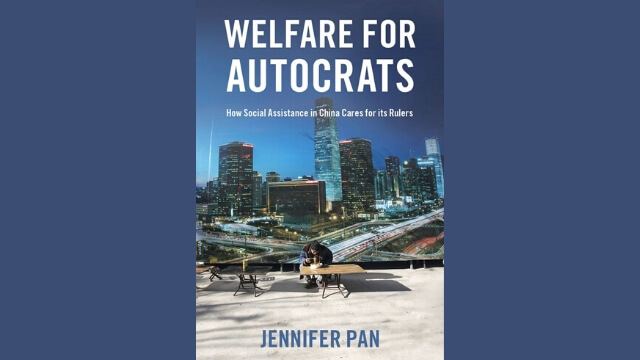
中國福利的失敗
《獨裁者的福利:中國的社會救助制度如何為統治者服務》(「Welfare for Autocrats: How Social Assistance in China Care for Its Rulers」,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年出版)是一本出色、專業性很強的研究類書籍。讀者不會預料到會在此書中看到關於宗教的內容,但其實是有的,而且並非不重要。
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助理教授詹妮弗·潘(Jennifer Pan)的這本書對中國「低保」制度進行了研究,該制度被標榜為「世界最大無條件現金轉移計劃」,也是旨在「消除貧困」的兩大中國福利支柱之一。另一支柱是特困人員救助計劃,但是近年來,特困的重要性降低了,而低保的重要性卻有所提高。
中國的統計數據總是強調對窮人的照顧,但卻暴露出一個嚴重不平等現象。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雖然中國的經濟增長了,但全國「城市失業工人卻多達6000萬人」。到2015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國民收入份額增至41%,而收入最低的50%人群的收入份額降到15%。」中國的宣傳可以反駁美國有同樣的數據,但是美國並沒有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或平等主義國家。
詹妮弗·潘說,中國的「福利制度加劇了貧富分化,而不是縮小了貧富差距」。富人和腐敗階層操控這些制度的手法變得非常嫻熟。
低保登場
中共推出低保制度是為了解決上述問題的一種手段,1993年6月在上海首先試行。1997年9月2日,城市低保在全國推行;2007年7月,農村低保在全國推行。2003年,居民領取城市低保達到高峰,共有2250萬人,而領取農村低保的居民竟達5390萬人。後來這些數字有所下滑,2017年領取城市低保的下降到1260萬人,領取農村低保的下降到4050萬人(相比之下,領取低保的特困戶總共才470萬)。
低保與最近在意大利推出的有爭議的「全民基本收入」(reddito di cittadinanza)相似。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每個月都能領到一筆現金。問題是,如何確認這些人「無法工作」。
詹妮弗·潘解釋道,在中國,「無法工作」的人分為兩類。屬於第一類的人由於個人殘疾或就業市場的問題而無法工作。但屬於第二類的人卻是因為中共寧願他們不工作,並要求他們待在家裡接受「再教育」。這只是中共所謂的「目標類別」的其中一部分。「目標類別」是毛澤東1956年提出來的說法,官方公布了一份「目標類別」名單,並將「涉嫌參與邪教(遭查禁的宗教團體)、宗派、會道門或非法宗教活動」等列入其中。
在家接受再教育
詹妮弗·潘說,1999年法輪功組織示威抗議後,低保發生了很大變化。雖然中共最明顯的反應是「重拳出擊」,包括「大規模抓捕、關押和處決(示威者)」,但法輪功其實「已經改變了中共維穩」的方式。中共意識到,「重拳出擊」是必要的,但還不夠。法輪功抗議事件後,中共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改為「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內容包括兩方面,一是「重拳出擊」,二是詹妮弗·潘所說的「將安全系統『滲透』到文化、教育和福利中去」。
詹妮弗·潘認為,有一個普遍的錯誤觀念就是,中國的「再教育」只發生在教育轉化營、監獄這類機構裡。實際上,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是在家接受「再教育」的。「由居委會工作人員、樓長、當地警員、社區觀察志願者以及社區一級的黨員積極分子和幹部組成的再教育隊不定期上門拜訪這些家庭,他們的任務就是定期回訪再教育對象。」接受再教育的人花了太多時間接受再教育,以致他們無法找到一份固定工作,中共也認為讓他們去上班並非是個好主意,他們很有可能在單位「腐化」其他人。所以這類人可以領低保。
若要領低保,就要接受更嚴密的監視,事無鉅細地彙報個人的日常生活。不僅「以發放福利的名義實施監視不會那麼引人耳目」,而且「監視、義務、依賴」三角關係也因此得以形成。依中國人的心態,領取低保的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覺得自己有義務配合當地給他們發錢的政府人員的工作。他們也知道自己的名字會在社區公開,鄰里們都希望他們作為低保發放的對象能有忠心的表現。詹妮弗·潘指出,最後,他們領到手的這點錢不足以讓他們隨意採取行動反對中共,但已足以讓他們覺得自己得「依賴」中共。
低保淪為鎮壓遭查禁宗教的工具
詹妮弗·潘在中國實地考察並記錄了低保的運作方式,發現低保常常涉及宗教信仰,這也許令她感到有點意外。她講述了來自陝西西安的趙先生一家的遭遇。在岳母經診斷患有癌症之前,趙是一位對宗教信仰不太感興趣的工程師,但因岳母的病,他與被定為「邪教」的門徒會的信徒一起禱告,最後他岳母的病治好了,全家人於2012年加入門徒會。
這一家人接下來的遭遇展示了中共是如何將「重拳出擊」與各種形式的維穩手段相結合的。趙先生被抓坐牢,關進教育轉化營。他的親屬卻沒有被關進監獄,他們遭到監視,被安排參加一個與低保綁定的在家接受再教育的計劃。詹妮弗·潘採訪了一名姓楊的樓長,她負責給趙家發放低保。她坦言承認,她的工作目的是用軟硬兼施的手段將這家人從「危險的信仰」中「拯救出來」,如果趙家人答應放棄禱告和其他宗教活動,就提高他們的福利發放標準。
還有一類屬於用低保綁定在家接受再教育的人,包括那些被抓捕後來獲釋但當局認為他們接受的再教育尚未結束的人。詹妮弗·潘遇到的兩名領取低保的法輪功成員就屬於這種情況。他們也許不僅沒有被再教育完全轉化,反而「表現得極度恐懼,非常希望能擺脫政府的監視」。
簡而言之,低保已逐漸成為「鎮壓和監視的工具」,「一種維護政權的工具,不是照顧百姓,而是照顧中國的統治者」。
中共面臨的一些問題
低保的「硬性救助」並非沒有問題。首先是費用高,中國的財富也不是取之不盡的。主要為了監視「目標類別」的群體以及支持在家再教育,其結果意味著,領取低保的這些人的數量不斷增加,而那些由於非政治原因應該領取低保(即真正的窮人)實際卻沒領取到的人的數量將越來越多。這樣會導致抗議,可能威脅到低保的政治用途原本要維護的穩定。
但是,中共並不擔心這種「強烈反對」。總體而言,中共不喜歡人們抗議,但它認為經濟抗議沒有呼籲民主或宗教自由的抗議那麼危險。
最後,詹妮弗·潘提出一個問題:既然中共在中國安裝了3億個監控攝像頭,已達到了創紀錄數量,社會信用體系和高科技保證了全天候監視全世界人民,那麼2020年還需不需要保留低保的政治用途呢?詹妮弗·潘的回答與一些批評中共的人不同:中共知道高科技不能保證萬無一失。她提到,例如,警察數據庫(PoliceNet)並非沒有漏洞,也並非所有犯罪行為都記錄在上面。對於所有的科技反烏托邦,中共非常清楚高科技永遠無法完全取代逐人逐戶的人工監視。因此詹妮弗·潘認為,在家接受再教育的計劃以及利用低保達到監視目的還將繼續下去。
西方的監視專家可能會認為,這種高科技監控與人工監視相結合的龐大網絡風險(後者主要基於間諜和干預)導致出現大量的「假陽性」(即被劃為對中共政權構成威脅,而實際上對其無害的民眾)。然而,詹妮弗·潘得出的結論是,所有的制度都應在「精準」(將假陽性的機率降到最低)和「聯想」(將假陰性的機率降到最低,在本文所述的案例中,指的是那些可能對中共確實構成威脅卻未被發現的人)之間進行選擇。她說,在新疆,千千萬萬的維族人和其他絲毫沒有做過「對中共政權有任何威脅的人」仍然被關押在教育轉化營裡,這證明習近平領導的中共選擇的模式是「聯想」而非「精準」。用一句非技術的術語來說,中共寧可錯將數百萬無辜者關進監獄,也不放過一個罪犯(即反對中共政權的人)。